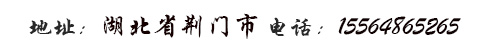李桂奎中国小说理论该如何打造自己独有
|
白癜风标本兼治 http://pf.39.net/bdfyy/bdfzj/160310/4784984.html 摘要:相对于较为早熟且能自成一定谱系的诗文、戏曲、书画等理论而言,小说理论主要以序跋、评点、杂论以及小说话等随感形式呈现,显得较为零散,有进一步系统化整合、提升、建构的空间。 近些年,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实绩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和“史论”撰写等方面,而在谱系建构方面则多停留于热切呼唤层面上,期待基于术语考释以奏其效。其具体操作流程大致是,先将搜辑而得的零散的概念、范畴以及命题等术语进行分级、分层、分类,使之成为不同系列的术语家族和术语族群;继而搬弄古老的解字释名、考镜源流、梳理脉络等传统学术路数,做到“释名以章(彰)义”。 继而,顺应近现代以来各类文论术语考释的劲势,借鉴中外阐释学、谱系学,尤其是“关键词”研究的学术经验,圆通地对各种小说批评术语的历史文化蕴涵、文艺审美蕴涵展开阐释。 最后通过类性脉络梳理,建构富有系统性的中国本土特色的小说理论谱系。 关键词:考释;考镜源流;脉络梳理;圆通阐释;术语家族;谱系建构在当今文论建设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与其生吞活剥地套用某些体系化的西方文论,或口号性地呼吁“现代阐释”“现代转换”以及“现代重建”,倒不如遵从前人扎扎实实的考辨阐释路数,建构一套富有中国气派、东方气质的本土化、自主性理论谱系。 一方面,相对于尚且拥有依稀可辨的谱系性的诗文理论、书画理论、戏曲理论而言,以各种序跋、评点、杂论以及小说话等形式存在的小说批评理论更多地给人以“寓目散评”“体系模糊”“碎片化”“拼盘化”等印象,因而期待借助古今贯通、中西打通等圆通学术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中那些多元性、富有张力的术语进行考释,并通过探其语义源流,发其衍生意蕴,以滋补和增强中国传统小说批评理论的元气和底气。 另一方面,要将小说批评中那些松散的碎石瓦片建构成较为严密的理论谱系,使之发挥更大的批评鉴赏效力,也理应从最为基础的、具体的术语考释和阐发来做起。 一、古典考释及其与小说名实阐释之互通 众所周知,术语是文学批评的主要构成要素,也是文艺理论言说或表达的工具。 这里所谓的“术语”,既包括以往文艺理论研究中“称名”“概念”“范畴”“命题”等名堂不一的术语,也包括近年西方文论所谓“关键词”意义上的术语。 可以说,大多数文艺理论术语的命名是经过一番词汇遴选与长期文化积淀的,其意义指向大致有义理与艺理二端。 在传统富有张力的“言意”观念下,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也大致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点展开。无论是望文生义的宏观概释,还是与时俱进的微观细释,都应尽量还原或拈用中国文论本色的诗性话语。 从文体学与阐释学双重视角看,“小说”固有的“说”“传”以及“演义”等术语的生发功能均可以与传统解释之学、传注之学、衍生之学形成某种呼应和关联,因而也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互通。 “考释”一词,最早见于清人阮元《小沧浪笔谈》卷二:“篆文奇古,予为考释之。”[1] 尽管作为一个词语出现较晚,但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它却由来已久。大概从古代说文、释名、解义等方法启用,考释行为就开始了,至今仍行之有效。 考,至少包括考其原始、考镜源流等内涵。 释,既包括释其内涵、研精阐微,也包括新意生发等。 在中国古代,以“解字”“释名”为名义的术语考释活动不仅源远流长,且历久弥新。其中,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著作开创了探求字义根源和阐释事物名、源的学术传统。 考释之道看似并不复杂,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由于术语的命名与创生至少应符合自洽性和有效性两条原则,因而术语考释也应以自洽性和有效性为旨归。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传统形态的考释法打上了较为鲜明的经学印记。 诞生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背景下的以分析古书章节句读为主的“章句之学”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不仅今文经学派自身颇擅此道,而且其“音韵”“文字”“考据”等注释经典的方略也常常被引入其他术语考释中,有效地发挥文论衍生作用。 可以说,包括小说评点在内的文学批评方式多生发于章句之学,许多文论术语释解“注重对文本的结构、意象、遣词造句等属于文学形式方面的分析,同时也不废义理和内容的考察”[2],在注重细微的注释和分析过程中,采取了“依经立义”“立象尽意”等言说方式。 当然,汉代以来古文经学家所提倡的“我注六经”,即以文字训话、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今文学家所从事的“六经注我”,即借助经典来阐述时代精神或发挥自己的新见解,对考释法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就小说批评术语考释实施而言,除了基本的字义、词义诠释,从命名视角阐释术语本身的意义、衍生的意义更为重要。 依据传统名实文化,参照当今语义学阐释方法,从命名视角考释古代小说批评术语,有助于有针对性地考察古代小说作法及其文本审美规律。 《阮元集》 历史地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典形态的考释法已趋于成熟。 不仅儒家的章句之学已颇成气候,而且对佛教经论里出现的术语加以解说的“格义”法也开始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其突出表现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汉代以来解经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考释之道。 其中,《书记》篇明确道:“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这里所谓的“解释结滞”是指解释行文中的不明之义,即刘勰在《序志》中进一步讲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3] 这些方法皆属于推原起源和演变,一言以蔽之曰“考”;这里所谓的“章”,即“彰”,所谓“释名以章义”是指从解释事物的名物入手,并进而将其含义放大,一言以蔽之曰“释”。 基于此,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校勘学以及目录学思想,对传统学术路数做了精辟概括。[4] 总之,考释之“考”主要在正本清源、考镜源流,讲求文献依据;“释”主要在通过脉络梳理加以阐发诠释,讲求符合文化传统与历史语境。 再后来,历经延承今文经学的解释方略的宋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洗礼,尤其是经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随后的叶燮等文论家创造性发挥,考释法的义理考索与艺理思辨精神得到强化,滋养着方兴未艾的小说批评。 到清代乾嘉时期,古文经学发展为盛极一时的朴学,主要集中于文字学或考古学,尽管对以往经世致用学术观念有所消解,但其所擅长的训诂、考订方法及其形成的求实严谨学风,对当今包括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考释在内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明清小说批评术语之考释接受了八股文观念阐释的影响,偏重于文法揭示,并显示出一定的重文字、音韵等训诂注释的特点。 当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与小说批评术语问题既可纳入阐释学视野来审视,反过来也可以用中国阐释学观念重新认识传统小说文体及其文本评语。 刘勰《文心雕龙》在采取“释名以章义”方法进行文体辨析时常用“音训释名”。其《论说》部分是这样解释“说”字的: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5] 尽管在整个讨论中刘勰针对的是文体或文章,但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关于“说”的阐释方法与“小说”批评术语之考释联系起来,由此进一步加深关于小说娱悦性的认识。 再看,古代小说作品题名多含“传”“记”,固然是受史传文学影响使然,但也可以与传统阐释学中的“传注”结合起来看。 关于“传”“记”“说”等方式的阐释学属性,李春青曾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注之学就是中国古代的经典阐释学。”“在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史上,‘传’是最早的阐释方式。”“除‘传’之外,较早的经典阐释方式还有‘记’和‘说’。”[6] 在古人多种多样的诠释观念中,除了用以表明解释而又成为小说篇目命名的“传”“记”“说”等术语之外,“演义”一词也含有阐释学与文体学双重功能。 就“演义”一词而言,它也作“演绎”,一开始便是作为注疏学概念而使用的。作为一种方法,它常被用以解释词意,考证名物等等,自然被“考释”学术方法吸取借鉴。 况且,在语义演变发展中,“演义”一词既保留了固有的“释法”之义,又具备了作为小说“文体”的特点。 《在园杂志》 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曰:“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7]这种解释显然是针对小说创作融入更多虚幻、荒诞观念成分而进行的。 关于“演义”之原初,近代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看得较清楚:“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8] 无论是“演言”还是“演事”,都具有推演阐释性质。早期“演义”的一种功能是,小说家依据经典来演说上世故事,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作适当的“增饰”。 从阐释学视角看,“传述”“记述”“演义”自然都属于对原文本进行解说、解释、发挥的重要方法;而从文体史视角看,无论“传”“记”,还是“说”,又都是小说文体的某种重要形式或形态。 这种创作方法与阐释方法的彼此呼应也为我们推动小说批评术语考释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思路。 概而言之,传统文论发展中形成的以文献考据与义理阐发为重心的古典术语考释法起源于“解字”“释名”,后在经学以及佛学等阐释观念影响下,形成刘勰所谓的“释名以章义”方法,再加其他固有的“音训释名”“以类证义”方略,对文论术语原初含义与后来衍生意义阐发具有普适性与长效性。 就小说批评术语研究而言,古典术语考释方法可谓得天独厚:一方面,依托于“解字”“释名”“彰义”等常规术语考释,处于零散状态的小说批评术语可以得到整合、建构;另一方面“传”“记”“演义”等小说体式本身含有解释性质,自然与小说批评术语考释存在天缘作合,渗透或寄生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自释中。 如此说来,术语考释的过程也是一个小说理论不断生发、推演、提升的过程。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二、古典考释的现代化及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之实绩 作为抽象化理论概括的结果,各体文论术语中的很大一部分既生发于具体的各体文学实践,又期待依托考释不断地发扬光大。 纵观中国文论研究史,人们在史的梳理与理论建构上常常以术语阐释为基础。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以及各种蜂拥而来的新思想、新方法的渗透和影响下,古典形态的术语考释得以脱胎换骨,并被广泛且有效地应用于各种文学批评史编写和文论研究。 从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年版)开始的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往往依托于对历代文论中富有活力的概念、范畴、命题等术语加以考释。 尽管一开始人们并没有采取“术语考释”或“话语阐发”等名义去践行,但却已显示出某种践行这种学术路数之实。 直至近年,随着术语考释法的不断演进,新推出的“马工程”教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仍主动选择立足于文论术语考释。其主编黄霖先生确定的编写理念是: “系统展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主要内容、重要范畴与基本术语,旨在梳理与彰显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为当前重建具有中国特色、又立足当今现实,并适应全球文化潮流的文论体系铺路。”[9] 这尽管是针对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普适性学术方法而言的,但对于传统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蓦然回首可见,20世纪上半叶,许多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一代学人,包括王国维、闻一多、郭绍虞、朱自清、罗根泽、朱光潜、宗白华、吴宓、陈寅恪、钱锺书、王瑶等文史学者,都曾凭着颇见功力的文论术语考释,一展开疆拓土的雄风。 其中,王国维得风气之先,率先引领起从古典形态术语考释向现代术语考释的转型,不仅推出《论性》《释理》《原命》《释史》《释由》等文章,对古代文化中的几个核心术语进行了考释,而且还在《人间词话》中对其提出的影响深远的“境界”这一重要术语进行了重新命名、考释、建构。继而,在术语考释的现代化方面,郭绍虞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先是对“性灵”“神韵”“格调”等术语展开考释,写成《性灵说》《神韵与格调》二文;然后将其纳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论著之中,使之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构的奠基之作。 随之,朱自清不仅对郭绍虞开辟的研究范式和治学方法深表认同与赞赏,而且还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指出: “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 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情’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10] 强调懂得某些术语意义对于懂得这些术语所处某一时代或所属某一理论家学说的重要性。 继而,朱先生先后身体力行地运用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对“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等诗论术语及其内在联系,展开较全面而深入的考释。后来汇成影响深远的《诗言志辨》一书。 在这种学术风气影响下,朱自清所提到的各种标志性文论术语也陆续得到考释,代表性成果有,吕雪堂之释“风骨”()、张寿林之释“神韵”()、许群之释“意境”()、傅庚生之释“赋比兴”“神气”()等等。 如此,经过王国维、郭绍虞、朱自清等一代学人的努力,古代文论固有的术语考释传统被大张旗鼓地从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对郭绍虞、朱自清等先生在现代学术史上所做的筚路蓝缕的更新换代考释工作,陈平原曾纳入“关键词”视野审视,称之为“以文学观念的演进为中心来构建批评史的研究框架”“借考证特定词汇的生成与演变,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1] 对这种从小处入手,以“精密分析”“仔细的考辨”为特点的术语考释方法及其在中国文论现代化与本土化的过程中所发挥出的特有效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再看,20世纪下半叶以来,基于术语考释方法的文论研究成果更是不绝如缕。颇具代表性者有,钱锺书的《管锥编》(中华书局年版)和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年再版时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新增6篇文章)。 前者长于通过引经据典并善于通过跨越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等壁垒,对经史子集之文化符号及各种语词展开考论,不执著于术语考释却拓展了术语考释的方略; 后者运用“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等方法,以熊十力“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理念为行动方针和指导原则,既本着“根底无易其固”原则以概释其词,又根据“裁断必出于己”方针以细释其义,并借助对相关术语展开全面深入的比较,对《文心雕龙》中的各种创作论术语进行了严谨细致的考论,从而建构起“心物交融”说、“杼轴献功”说、“作家才性”说、“拟容取心”说、“情志”说、“三准”说、“杂而不越”说、“率志委和”说等“八说”理论体系。 此后,术语考释法不仅成为打开“文心”的一把金钥匙,而且也成为开启“龙学”宝库的一道重要法门。 特别需要称扬的是,童庆炳围绕其“文化诗学”理念,积二十多年之功,分别从语言之维、审美之维、文化之维三个维度,对《文心雕龙》中的“道心神理”“奇正华实”“会通适变”“因内符外”“循体成势”“感物吟志”“披文入情”等三十个具有命题性质的术语进行了深度考释与解说,汇集为《〈文心雕龙〉三十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显示出中西会通、古今贯通等现代综合研究的力度和水平。 总之,现代学者们凭着较强的辨析、思辨意识和功力,围绕《文心雕龙》这一经典文论所展开的系列术语考释,发挥了引领学术转型的重要作用。 期间,在新的思想观念影响下,许多学者除了广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etzhiqiguanyana.com/zqgyfz/9447.html
- 上一篇文章: 有了这项新技术,嵊州人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